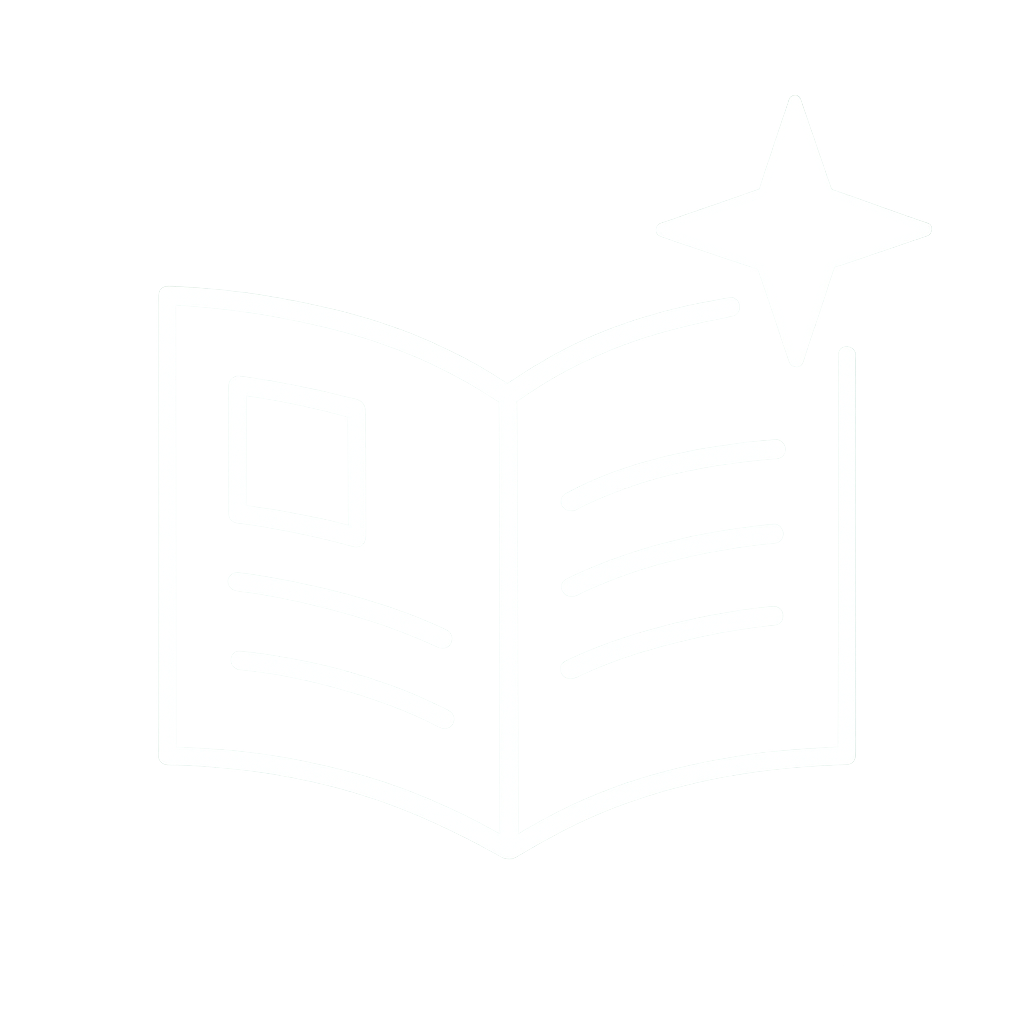半年多的服藥期過後,我發現吃這些藥片帶來的副作用遠遠大於它們給我的正面作用。於是我就這麼草率地斷藥了,在醫師沒有允許的情況下。
那種感覺就像是人突然披上了鐵衣,腦子裡的記憶線段被七零八落地切成拼不起來,找又找不見的毛線尸塊。顏色和聲音,興趣和厭惡都離你而去,只剩下不想思考的頹廢的自己縮在角落裡,無力地呻吟著。
但是也有好處,至少我從藥物營造的“我很健康”的錯覺裡抽身離開,回到腳踏實地的現實裡來了。我有權利選擇刀或是藥,墜樓或是人格改造……雖然這麼說有些太過於負面,但皮肉被劃開的感覺,血液漫出來流進嘴唇和舌頭的感覺,比在虛浮的假象裡自欺欺人好的多的多。
半年多的服藥期過後,我發現吃這些藥片帶來的副作用遠遠大於它們給我的正面作用。於是我就這麼草率地斷藥了,在醫師沒有允許的情況下。
那種感覺就像是人突然披上了鐵衣,腦子裡的記憶線段被七零八落地切成拼不起來,找又找不見的毛線尸塊。顏色和聲音,興趣和厭惡都離你而去,只剩下不想思考的頹廢的自己縮在角落裡,無力地呻吟著。
但是也有好處,至少我從藥物營造的“我很健康”的錯覺裡抽身離開,回到腳踏實地的現實裡來了。我有權利選擇刀或是藥,墜樓或是人格改造……雖然這麼說有些太過於負面,但皮肉被劃開的感覺,血液漫出來流進嘴唇和舌頭的感覺,比在虛浮的假象裡自欺欺人好的多的多。
就我而言,這世間不存在任何一個我認為可以談戀愛的人——自願把情緒,過去,現在甚至是幾十年以後的未來都親手交給另一個我現在甚至對他(她?)一無所知的人,讓對方擁有對我的一定程度上的掌握權,這種事情會讓我感到極度的不安與失控。就像人不會把心臟剖出來交給狗一樣。
但是人又不是完全地不渴望愛。比如我,在無數個夜晚的夢中,總有一個看不清面容的身影站在我身旁。在那些一起歡笑,哭泣,擔憂,憤怒的時間裡,在每次醒來悵然若失,委屈、失落和期待一起湧上來的時候,在我每次嘗試描繪的未來裡無獨有偶地出現他那光線直穿軀體映射在地上的身影時…我可以大膽地說我是熱烈地,誠摯地愛著對方的。
就我而言,這世間不存在任何一個我認為可以談戀愛的人——自願把情緒,過去,現在甚至是幾十年以後的未來都親手交給另一個我現在甚至對他(她?)一無所知的人,讓對方擁有對我的一定程度上的掌握權,這種事情會讓我感到極度的不安與失控。就像人不會把心臟剖出來交給狗一樣。
但是人又不是完全地不渴望愛。比如我,在無數個夜晚的夢中,總有一個看不清面容的身影站在我身旁。在那些一起歡笑,哭泣,擔憂,憤怒的時間裡,在每次醒來悵然若失,委屈、失落和期待一起湧上來的時候,在我每次嘗試描繪的未來裡無獨有偶地出現他那光線直穿軀體映射在地上的身影時…我可以大膽地說我是熱烈地,誠摯地愛著對方的。
窗外的雨聲大得出奇,雨點噼里啪啦打在玻璃窗上,再一片片滑下來。暖黃色的燈光從頂上懶洋洋地罩下來,桌上的米白色杯子裡裝滿還冒著熱氣的榛果拿鐵。
我和他坐在鋪著白色兔絨毯的沙發上,面對面,抱著吉他哼著歌。泛音從指尖一個個散著步慢悠悠地走,兩個人的聲音時而重疊時而分開,纏纏綿綿,溫柔繾眷,像一旁的窗子上打著圈往下滑的水滴。
窗外是都市的燈柱林立,樓與樓之間是散落在墻壁上的繁星點點,再往遠看,一片水霧看不真切的地方,有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到達的未來。
但是我們是不會怕的,畢竟有音樂,有彼此,還有這場漫無目的又似乎會持續下到漫過世界盡頭的雨。
窗外的雨聲大得出奇,雨點噼里啪啦打在玻璃窗上,再一片片滑下來。暖黃色的燈光從頂上懶洋洋地罩下來,桌上的米白色杯子裡裝滿還冒著熱氣的榛果拿鐵。
我和他坐在鋪著白色兔絨毯的沙發上,面對面,抱著吉他哼著歌。泛音從指尖一個個散著步慢悠悠地走,兩個人的聲音時而重疊時而分開,纏纏綿綿,溫柔繾眷,像一旁的窗子上打著圈往下滑的水滴。
窗外是都市的燈柱林立,樓與樓之間是散落在墻壁上的繁星點點,再往遠看,一片水霧看不真切的地方,有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到達的未來。
但是我們是不會怕的,畢竟有音樂,有彼此,還有這場漫無目的又似乎會持續下到漫過世界盡頭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