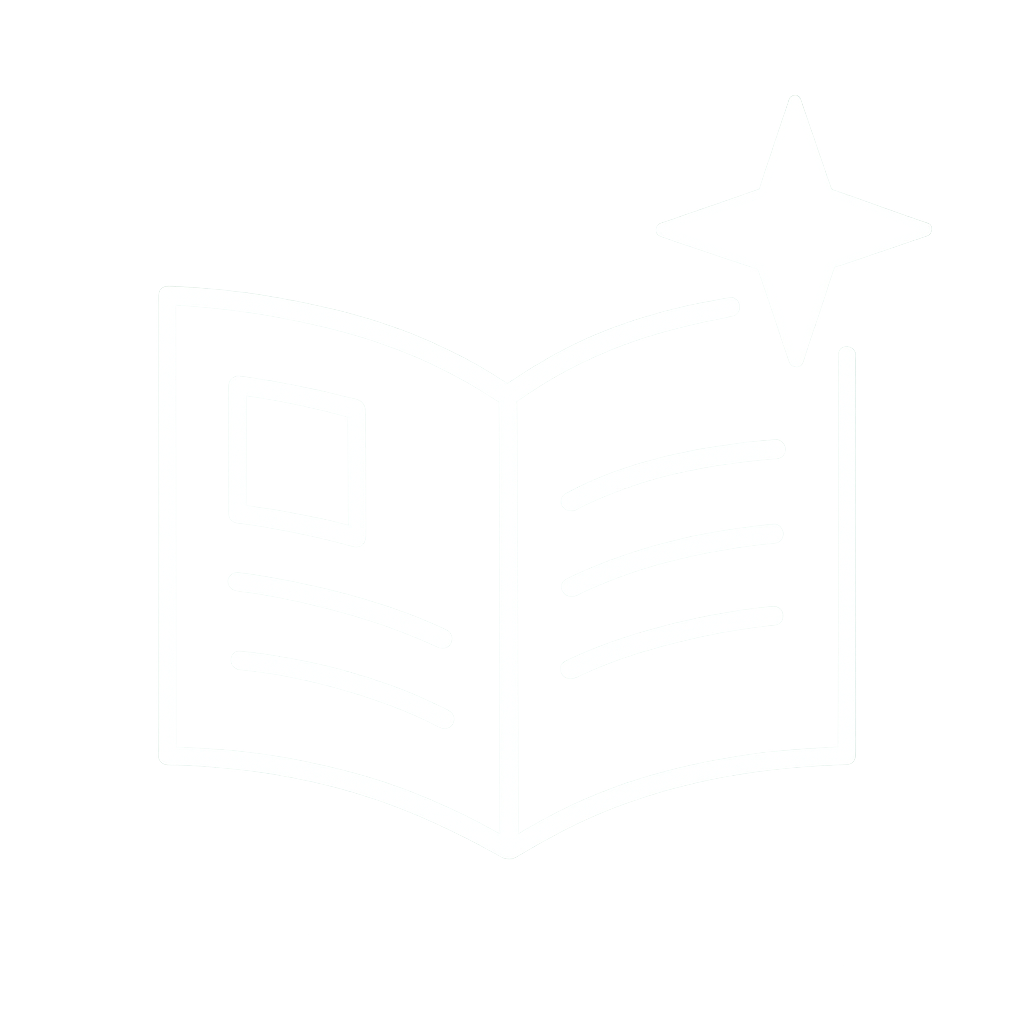我想,在言論自由的世界,表達想法不只是個人權利,也是隱性義務;唯有把話說出來,才有機會讓他人知道有這樣的聲音,也才能讓這個世界持續接受多元意見。因此,只要人人清楚自己所言的應負責任,我認為接受此景亂度較大應為自然。
基於此境,難免意見相左,而希望打破僵局或找出方向的人,勢必肩負聆聽、觀察、理解、整理的責任,在諧音和噪音中尋找基頻,進而探索共振的可能性。
「我們都想讓事情變得更好」是我迄今常用的基本認知,在這之上再討論各自認為的「好」為何物,求同存異互相尊重,理想上能有進展,或至少有個抒發方向。
我想,在言論自由的世界,表達想法不只是個人權利,也是隱性義務;唯有把話說出來,才有機會讓他人知道有這樣的聲音,也才能讓這個世界持續接受多元意見。因此,只要人人清楚自己所言的應負責任,我認為接受此景亂度較大應為自然。
基於此境,難免意見相左,而希望打破僵局或找出方向的人,勢必肩負聆聽、觀察、理解、整理的責任,在諧音和噪音中尋找基頻,進而探索共振的可能性。
「我們都想讓事情變得更好」是我迄今常用的基本認知,在這之上再討論各自認為的「好」為何物,求同存異互相尊重,理想上能有進展,或至少有個抒發方向。
一開始很明顯,甚至不需要查證,就能知道LLM只是善於堆砌文字的應答機;因此,AI幻覺的影像已存人心。隨其迭代,儘管其真確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仍對其輸出有所保留,謹慎程度甚至高過於注意其他人類所傳播的「幻覺」。
不過說到底,總有一天,這些幻覺仍會被習慣,而習慣總是不易察覺;未能被察覺的幻覺,對接收者來說,稱不上幻覺。
一開始很明顯,甚至不需要查證,就能知道LLM只是善於堆砌文字的應答機;因此,AI幻覺的影像已存人心。隨其迭代,儘管其真確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仍對其輸出有所保留,謹慎程度甚至高過於注意其他人類所傳播的「幻覺」。
不過說到底,總有一天,這些幻覺仍會被習慣,而習慣總是不易察覺;未能被察覺的幻覺,對接收者來說,稱不上幻覺。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夫以AI為鏡,可以見何世?
當年對弈AlphaGo的李世乭認為,在AlphaGo之前的舊棋譜只剩歷史價值,因為AI下的棋譜品質更高;棋手研究AI棋步,可以學到更多。我想這代表,AI能創造許多嶄新的思路,更勝人類以往累積的經驗。
我的想法是,人類的經驗如神農嚐百草,數千年的歷史傳承,仍有物理上的速度限制,而演算法在棋盤上的對弈在模型發展的劇進下卻能以毫秒快速迭代趨吉避凶。這可能是在符合棋盤規則下的隨機煉蠱結果,不過,如果今天AI處理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的邊界和規則呢?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夫以AI為鏡,可以見何世?
當年對弈AlphaGo的李世乭認為,在AlphaGo之前的舊棋譜只剩歷史價值,因為AI下的棋譜品質更高;棋手研究AI棋步,可以學到更多。我想這代表,AI能創造許多嶄新的思路,更勝人類以往累積的經驗。
我的想法是,人類的經驗如神農嚐百草,數千年的歷史傳承,仍有物理上的速度限制,而演算法在棋盤上的對弈在模型發展的劇進下卻能以毫秒快速迭代趨吉避凶。這可能是在符合棋盤規則下的隨機煉蠱結果,不過,如果今天AI處理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的邊界和規則呢?
在網路世界,則常有不同的「空氣」組成;由於網路上的言論光譜更加多元而極端,所以如果將此空氣當成現實解讀,有時可能會像置身瘴氣之地或宇宙之中難以呼吸。因此,在閱讀這裡的空氣時,我總是需要有所準備;畢竟,我有時是會飛出同溫層去探索不同思路。
在網路世界,則常有不同的「空氣」組成;由於網路上的言論光譜更加多元而極端,所以如果將此空氣當成現實解讀,有時可能會像置身瘴氣之地或宇宙之中難以呼吸。因此,在閱讀這裡的空氣時,我總是需要有所準備;畢竟,我有時是會飛出同溫層去探索不同思路。
因此,當意識到有實體反饋的社會互動已明顯不如以往時,我並不確定原因是已經脫離了強制群體活動的規則,還是我把更多的時間用在與虛擬資訊交流;抑或只是在近年強調個人自主權的風潮下,我更專注於自我,減少了對他人的興趣。
因此,當意識到有實體反饋的社會互動已明顯不如以往時,我並不確定原因是已經脫離了強制群體活動的規則,還是我把更多的時間用在與虛擬資訊交流;抑或只是在近年強調個人自主權的風潮下,我更專注於自我,減少了對他人的興趣。
數年後,手機能直接提供的資訊更多了;我自問,學習還有什麼必要呢?
數年後,手機能直接提供的資訊更多了;我自問,學習還有什麼必要呢?
在二〇一〇年,Broome提出集體共享錯誤記憶的曼德拉效應。我想這種記憶與史實不符的情況,在越來越容易刻劃事實的時代,只會更難以迴避。雖然我期許自己能針對每一個資訊走完整個識讀脈絡,而非直接接受每個結論,但在資訊過載的世界,我想這還是不太可能。頂多只能對我認為重要的事情多加著墨。
在二〇一〇年,Broome提出集體共享錯誤記憶的曼德拉效應。我想這種記憶與史實不符的情況,在越來越容易刻劃事實的時代,只會更難以迴避。雖然我期許自己能針對每一個資訊走完整個識讀脈絡,而非直接接受每個結論,但在資訊過載的世界,我想這還是不太可能。頂多只能對我認為重要的事情多加著墨。
既然是分布,試著抽樣就能接近全貌;我想知道我的能力位階,試著與他人比較就能推論高低。關鍵是,要如何抽樣才能達成真正的隨機?
我認為很難,且非必要。能做的是認清抽樣的範圍是否偏差,及這個偏差可否接受。在學校班級中,我可以在某些方面勝過他人,進而瞭解自身天賦所在,最終培養出能養活自己的一技之長;但在網路各種神人面前,我只能相形見絀,早早放棄各種追求似乎比較輕鬆。
畢竟網路世界充滿倖存者偏差,作為參考目標,極佳。但以凡人之軀與外界互動,才能瞭解我的平凡價值坐落何處。
既然是分布,試著抽樣就能接近全貌;我想知道我的能力位階,試著與他人比較就能推論高低。關鍵是,要如何抽樣才能達成真正的隨機?
我認為很難,且非必要。能做的是認清抽樣的範圍是否偏差,及這個偏差可否接受。在學校班級中,我可以在某些方面勝過他人,進而瞭解自身天賦所在,最終培養出能養活自己的一技之長;但在網路各種神人面前,我只能相形見絀,早早放棄各種追求似乎比較輕鬆。
畢竟網路世界充滿倖存者偏差,作為參考目標,極佳。但以凡人之軀與外界互動,才能瞭解我的平凡價值坐落何處。
我始終懷疑著尋得意義的必要,或曰「夢想」。探究原因,是我對完美答案的過度追求,甚至連過程都希望優雅;但我做不到,想夢都不容易,夢想更難。
「努力就能成功;實現夢想,就能成為人生勝利組」這是北野武觀察到的日本近代價值觀。然而,在現實中,有才華者出人頭地,沒有才華卻滿懷希望的人卻只能在荒漠中尋寶。
「『我沒有任何才華,只想踏實工作、結婚、生子就好。』為什麼不能這樣想呢?」
因為這樣不有趣。
我想,為自己於內在世界保留特權,同時認知自己於外在世界的平凡,讓夢想回歸本質,讓腳步走得踏實,是我目前的答案。
我始終懷疑著尋得意義的必要,或曰「夢想」。探究原因,是我對完美答案的過度追求,甚至連過程都希望優雅;但我做不到,想夢都不容易,夢想更難。
「努力就能成功;實現夢想,就能成為人生勝利組」這是北野武觀察到的日本近代價值觀。然而,在現實中,有才華者出人頭地,沒有才華卻滿懷希望的人卻只能在荒漠中尋寶。
「『我沒有任何才華,只想踏實工作、結婚、生子就好。』為什麼不能這樣想呢?」
因為這樣不有趣。
我想,為自己於內在世界保留特權,同時認知自己於外在世界的平凡,讓夢想回歸本質,讓腳步走得踏實,是我目前的答案。
除了深度的旅行有時也是心靈的療癒,我也想到「縱觀效應」,一種太空人從宇宙望向地球時,感受到的認知變化。他們忽略了人類界定的疆界,將地球視為一個整體,而人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互相連結的命運共同體。所謂的日與夜,跟隨著地球的自轉呈現在眼前,這是地球居民共享的平等;而我們感受到的重力,也是生存在地球之上的證明。這一切從太空觀察,感悟格外明顯。
除了深度的旅行有時也是心靈的療癒,我也想到「縱觀效應」,一種太空人從宇宙望向地球時,感受到的認知變化。他們忽略了人類界定的疆界,將地球視為一個整體,而人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互相連結的命運共同體。所謂的日與夜,跟隨著地球的自轉呈現在眼前,這是地球居民共享的平等;而我們感受到的重力,也是生存在地球之上的證明。這一切從太空觀察,感悟格外明顯。
不像動畫作品中埋藏的彩蛋,更像是在網路世界中的那些,總會有人懂的,吹起同一個過濾泡泡中的人們才能看見的顏色。
在辦這個新帳號的時候,有感而發,但現在才發。
不像動畫作品中埋藏的彩蛋,更像是在網路世界中的那些,總會有人懂的,吹起同一個過濾泡泡中的人們才能看見的顏色。
在辦這個新帳號的時候,有感而發,但現在才發。
思考起意義讓我有種失去本能的感覺。回頭一想,或許意義存在於當下,或許我應該從在每一個小小時間內找到的愉悅與成就感做為出發點,累積出未來的方向。
思考起意義讓我有種失去本能的感覺。回頭一想,或許意義存在於當下,或許我應該從在每一個小小時間內找到的愉悅與成就感做為出發點,累積出未來的方向。
越思索著意義,越覺得興寐至今不確定有什麼意義,也就越難覺得當下的所做所為有什麼價值。可以說是不夠忙,所以有餘裕探究意義,但我仍認為思考這些仍是重要的。
越思索著意義,越覺得興寐至今不確定有什麼意義,也就越難覺得當下的所做所為有什麼價值。可以說是不夠忙,所以有餘裕探究意義,但我仍認為思考這些仍是重要的。
總之,我自然而然開始思考,不確定是否為了留存於傳說、歷史、記憶、感情、基因、智慧、演算、位元等之中。
至少,我能把一些碎片,僅存於當下。
總之,我自然而然開始思考,不確定是否為了留存於傳說、歷史、記憶、感情、基因、智慧、演算、位元等之中。
至少,我能把一些碎片,僅存於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