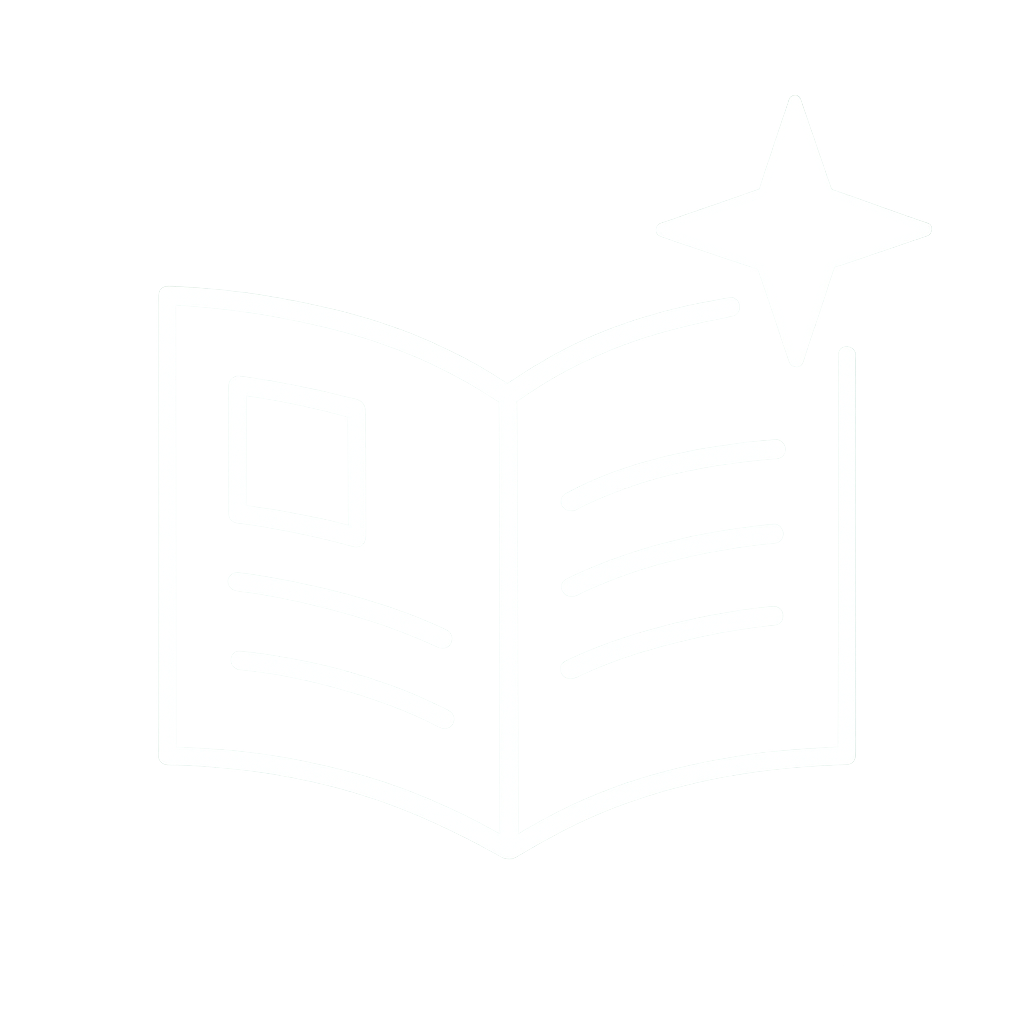我丟下電視,奪門而出去到高雄的海邊,浪潮淹沒我的腳印,那是和熱海煙火的岸很不同的沙灘。靜靜的,我才看見天藍色的遠方,有一種感動在朝我捲過來。
我終於坦承自己捨不得,我有後悔,有過兩難,也想過重頭來過,那黏糊糊勾住我的心的痛苦,當我坦承,才知道這也是一種感動。
我丟下電視,奪門而出去到高雄的海邊,浪潮淹沒我的腳印,那是和熱海煙火的岸很不同的沙灘。靜靜的,我才看見天藍色的遠方,有一種感動在朝我捲過來。
我終於坦承自己捨不得,我有後悔,有過兩難,也想過重頭來過,那黏糊糊勾住我的心的痛苦,當我坦承,才知道這也是一種感動。
成長過程中,某次開始整理房間時就學會了斷捨離,是因為隨著年歲增長,房間也終於容不下我一天一天的回憶。每丟掉一些曾經證明過我成長的東西,我總是想「過去能做到這樣,未來只會更好」。彷彿一句咒語帶我回到現實,可現在想來,不過是把過去投射到未來罷了。未來的可塑性,便這麼的被過去侵占,滿是過去的思念,這句咒語真成了咒語。
成長過程中,某次開始整理房間時就學會了斷捨離,是因為隨著年歲增長,房間也終於容不下我一天一天的回憶。每丟掉一些曾經證明過我成長的東西,我總是想「過去能做到這樣,未來只會更好」。彷彿一句咒語帶我回到現實,可現在想來,不過是把過去投射到未來罷了。未來的可塑性,便這麼的被過去侵占,滿是過去的思念,這句咒語真成了咒語。
下個瞬間我就回到家裡了,在黑漆漆的電視螢幕前發呆,一年就在電視裡經過了,螢幕留下的黑映照我素顏邋遢的睡衣。想著別再掙扎了,「過去」這個概念,是人類最初能夠閱聽的電影,是沒有實體的。
下個瞬間我就回到家裡了,在黑漆漆的電視螢幕前發呆,一年就在電視裡經過了,螢幕留下的黑映照我素顏邋遢的睡衣。想著別再掙扎了,「過去」這個概念,是人類最初能夠閱聽的電影,是沒有實體的。
已經交出去的鑰匙,用一絲一縷的念交織。我還是一直在打開房間的門,踏入鋪著一層灰的玄關,沿途在狹窄通道撿拾出門前亂扔的生活物品,然後照慣例洗手洗臉換衣,打開冰箱拿出茶與牛奶。
偶爾也還是會幻聽熱水放好的聲音。
已經交出去的鑰匙,用一絲一縷的念交織。我還是一直在打開房間的門,踏入鋪著一層灰的玄關,沿途在狹窄通道撿拾出門前亂扔的生活物品,然後照慣例洗手洗臉換衣,打開冰箱拿出茶與牛奶。
偶爾也還是會幻聽熱水放好的聲音。
搭地鐵時我喜歡從窗戶看外面的風景,有時經過河岸與橋,有時經過靜悄悄的小鎮,那種平交道還存在,放下欄杆還會發出噹噹聲響的小鎮。即使而過那些民宅,我總在想,住在這裡的人一天是怎麼過的?生活是怎麼過的?四季是怎麼過的?他們的日常他們的普通,於我這個外人,就像電影或小說一樣。
搭地鐵時我喜歡從窗戶看外面的風景,有時經過河岸與橋,有時經過靜悄悄的小鎮,那種平交道還存在,放下欄杆還會發出噹噹聲響的小鎮。即使而過那些民宅,我總在想,住在這裡的人一天是怎麼過的?生活是怎麼過的?四季是怎麼過的?他們的日常他們的普通,於我這個外人,就像電影或小說一樣。
我對死亡的印象,和書裡寫出的死亡,也不是同一種感情了吧。
我對死亡的印象,和書裡寫出的死亡,也不是同一種感情了吧。
最好的是,他很清楚我雖然偶爾語帶尖刺,但卻從來不會懷疑我是愛他的。
他是完全不受我影響的,一直有著一些被我覺得太過理想但又在心裡其實很欽羨很愛慕的的天真想法。
他這樣的人最好的就是他永遠不厭煩於我刺痛他,哪怕他偶爾也真的會被刺痛,但他不會氣餒我,不會覺得我可恨,相反地,他會認真的思考我的觀點看待我的感受。
他總是只被好的一面影響到。
最好的是,他很清楚我雖然偶爾語帶尖刺,但卻從來不會懷疑我是愛他的。
他是完全不受我影響的,一直有著一些被我覺得太過理想但又在心裡其實很欽羨很愛慕的的天真想法。
他這樣的人最好的就是他永遠不厭煩於我刺痛他,哪怕他偶爾也真的會被刺痛,但他不會氣餒我,不會覺得我可恨,相反地,他會認真的思考我的觀點看待我的感受。
他總是只被好的一面影響到。
這樣緊緊緊緊的互相擁抱都沒能消去離開大阪時我的心不在焉和失神,在車上我努力忍住不要哭。最後睡著了。在東京車站下車,一番舟車勞頓才回到宿舍。
這樣緊緊緊緊的互相擁抱都沒能消去離開大阪時我的心不在焉和失神,在車上我努力忍住不要哭。最後睡著了。在東京車站下車,一番舟車勞頓才回到宿舍。
是他不在我才需要依靠隨機的夢境稍微給我一些幸福的感受。真的就只是些微的感受而已。在夢裡我通常就知道這是夢了。
我和他也很常聊到夢,他總是說我為什麼能夠在夢裡知道這是夢,我說我不知道,或許這是一種天賦。但是認識他之後我覺得現實還比較夢幻呢。
是他不在我才需要依靠隨機的夢境稍微給我一些幸福的感受。真的就只是些微的感受而已。在夢裡我通常就知道這是夢了。
我和他也很常聊到夢,他總是說我為什麼能夠在夢裡知道這是夢,我說我不知道,或許這是一種天賦。但是認識他之後我覺得現實還比較夢幻呢。
原本其實也沒意思,從沒想過逛小七這件事有什麼特別,直到我又變成自己一個人逛小七。
一直想,要是他還在的話,我們會怎麼做,會怎麼講話聊天,他會怎麼阻止我買甜的,我又會如何對他甜言蜜語撒嬌。
原本其實也沒意思,從沒想過逛小七這件事有什麼特別,直到我又變成自己一個人逛小七。
一直想,要是他還在的話,我們會怎麼做,會怎麼講話聊天,他會怎麼阻止我買甜的,我又會如何對他甜言蜜語撒嬌。
很狹小的空間但是也因此很親密,我們總是要一直跨過彼此才能去洗碗、去洗手間、去洗衣服曬衣服。
然後他離開的第一天我從學校回家,沒有任何訊息,沒有距離的報告,沒有人等在那裡陪我逛小七。
很狹小的空間但是也因此很親密,我們總是要一直跨過彼此才能去洗碗、去洗手間、去洗衣服曬衣服。
然後他離開的第一天我從學校回家,沒有任何訊息,沒有距離的報告,沒有人等在那裡陪我逛小七。
我的午餐一向很好搞定,鮪魚美奶滋三角飯糰,偶爾聽他的健康建議多買一份海藻沙拉,因為其他沙拉都有我不愛的番茄。
我的午餐一向很好搞定,鮪魚美奶滋三角飯糰,偶爾聽他的健康建議多買一份海藻沙拉,因為其他沙拉都有我不愛的番茄。
社會對你施加了影響,而你在性方面的選擇反映了你這個人是如何被影響的,你看著螢幕後的那一面其實是你的思想的集大成。
性癖絕對不是天生的。
把社會放大一百倍看就是色情創作,把色情創作縮小一百倍看就是社會,性的根本就是政治。
所以才說以性作為表達的手法是一件太過草率太過方便的事情,太引人注目又易於拆解。
我現在想達成的更偏向於以非性的手段來表達性,但是去探討這沒有被明白刻劃出來的性時又會發現其實暗線是更大的政治概念。
社會對你施加了影響,而你在性方面的選擇反映了你這個人是如何被影響的,你看著螢幕後的那一面其實是你的思想的集大成。
性癖絕對不是天生的。
把社會放大一百倍看就是色情創作,把色情創作縮小一百倍看就是社會,性的根本就是政治。
所以才說以性作為表達的手法是一件太過草率太過方便的事情,太引人注目又易於拆解。
我現在想達成的更偏向於以非性的手段來表達性,但是去探討這沒有被明白刻劃出來的性時又會發現其實暗線是更大的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