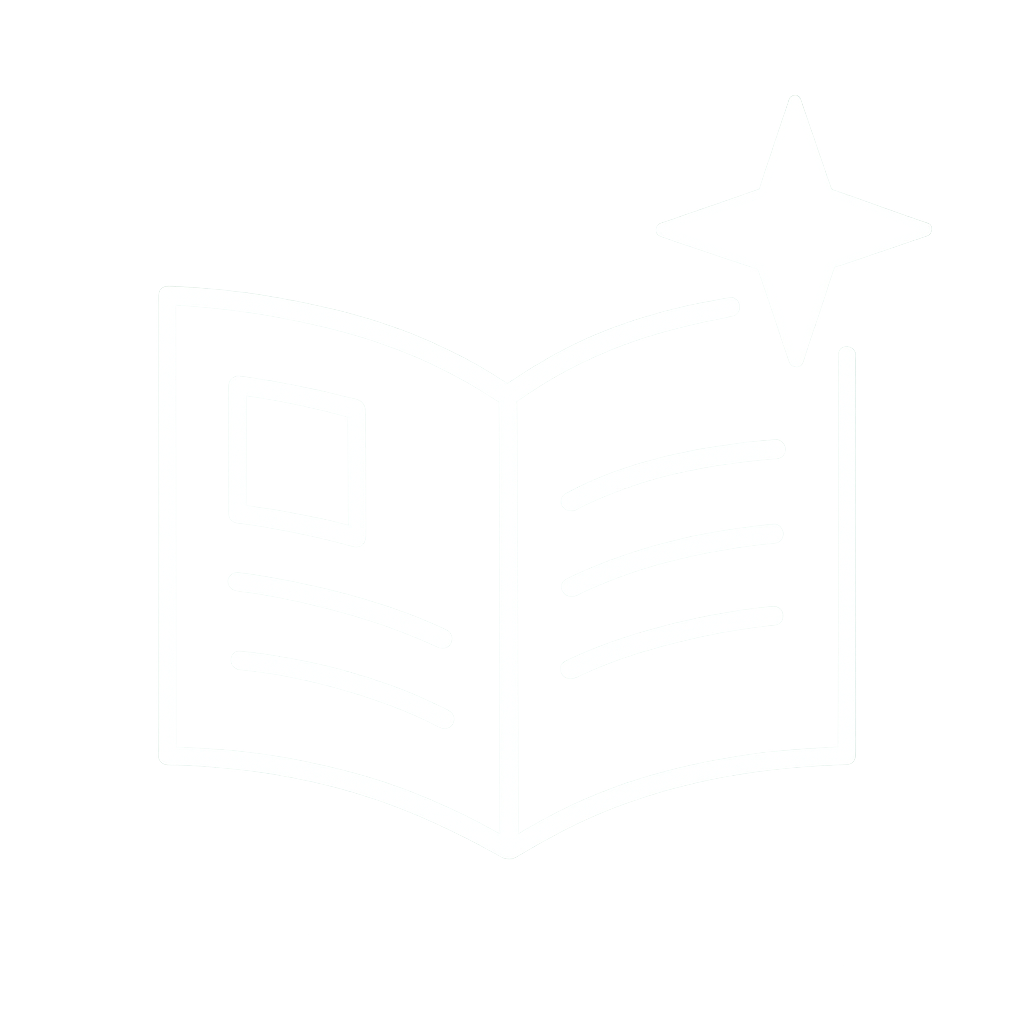不是喜歡回家,
只是沒有待在街上的理由。
已經好幾個月沒修剪頭髮。
媽似乎都快看不下去,
說女孩子別這樣抗桃抗敏。
想到我小時候的願望就是擁有一頭長直銀髮,跟犬夜叉一樣。
不是喜歡回家,
只是沒有待在街上的理由。
已經好幾個月沒修剪頭髮。
媽似乎都快看不下去,
說女孩子別這樣抗桃抗敏。
想到我小時候的願望就是擁有一頭長直銀髮,跟犬夜叉一樣。
想出家,以前很想幾乎是每天、總覺得世界與我無關;現在也是想,只是想的小聲,也沒敢再跟誰提這件事。跟媽說了,他說那誰來照顧她、誰都不願被拋下,關係中像是從來不存在你情我願。
S說這像是巨大的圖釘,你一輩子就被釘在這牆上。心莫名慌了一下、說的太過貼切也忘了怎麼回話。
安靜了一陣子,
S要掛電話前說,心煩就發篇文、總比憋死好。
想出家,以前很想幾乎是每天、總覺得世界與我無關;現在也是想,只是想的小聲,也沒敢再跟誰提這件事。跟媽說了,他說那誰來照顧她、誰都不願被拋下,關係中像是從來不存在你情我願。
S說這像是巨大的圖釘,你一輩子就被釘在這牆上。心莫名慌了一下、說的太過貼切也忘了怎麼回話。
安靜了一陣子,
S要掛電話前說,心煩就發篇文、總比憋死好。
真實的虛幻,海市蜃樓那般
大風,
像是蜷縮在金黃麥田,索性閉上眼
晃過許多影子、記不清,也沒來得及看清就散了。之後怎麼也想不起來,無端的惶恐、也沒睜開眼,想著自己忘了太多事,像是那些都是必然會被遺忘的。
必然,能記得的那一點成了全部、成了真實。想得太過痛苦了,只能接著想冰箱剩了什麼菜。




真實的虛幻,海市蜃樓那般
大風,
像是蜷縮在金黃麥田,索性閉上眼
晃過許多影子、記不清,也沒來得及看清就散了。之後怎麼也想不起來,無端的惶恐、也沒睜開眼,想著自己忘了太多事,像是那些都是必然會被遺忘的。
必然,能記得的那一點成了全部、成了真實。想得太過痛苦了,只能接著想冰箱剩了什麼菜。
阿嬤也塞了一些菊苣說喜歡吃沙拉這個也拿一點。
抱了一大把的菜,美好的週四清晨。
( 回家馬上烤了kale chips、大姐說太鹹了,也不知道怎麼抱持脆度🆘 不知道還有什麼食譜能夠消耗非常大把的羽衣甘藍?)

阿嬤也塞了一些菊苣說喜歡吃沙拉這個也拿一點。
抱了一大把的菜,美好的週四清晨。
( 回家馬上烤了kale chips、大姐說太鹹了,也不知道怎麼抱持脆度🆘 不知道還有什麼食譜能夠消耗非常大把的羽衣甘藍?)
穿著薄襯衫站在路燈下等計程車,知道自己看起來可能狼狽但也無心關切,只覺得身體空的不像話。
窗景不斷後退,在半開的窗戶間聽著蓄滿雜音的台語廣播,黃光一晃一晃擦過,明暗明暗,很drama的想著世間所有的事物我都看不清,突然一個瞬間意識全部聚焦眼前,無來由的感到惶恐,但也就那一下。
大拆大檢過後就很常這樣恍惚,總覺得面目全非但也懶得收拾。回家見大姐在客廳打電動、只開了半邊的燈,他頭也沒抬說「吃了沒,留了飯菜在電鍋。」
想著幾年後在很平常的瞬間可能會想起這一幕。



穿著薄襯衫站在路燈下等計程車,知道自己看起來可能狼狽但也無心關切,只覺得身體空的不像話。
窗景不斷後退,在半開的窗戶間聽著蓄滿雜音的台語廣播,黃光一晃一晃擦過,明暗明暗,很drama的想著世間所有的事物我都看不清,突然一個瞬間意識全部聚焦眼前,無來由的感到惶恐,但也就那一下。
大拆大檢過後就很常這樣恍惚,總覺得面目全非但也懶得收拾。回家見大姐在客廳打電動、只開了半邊的燈,他頭也沒抬說「吃了沒,留了飯菜在電鍋。」
想著幾年後在很平常的瞬間可能會想起這一幕。
S在電話裡說「 你的心怎麼就不能再柔軟一點。」
她說的很大聲,有點像是責備。
笑著回說「 身體僵直的都快彎不下去如何柔軟,身心都隨著年紀越發堅硬固執,一直僵著嘗試柔軟也是疲倦。」
聽見S小聲的嘆氣,能知道這是他的柔軟、在為剛才的強硬道歉。
短暫的空白、誰也沒接話。好像又開始下起小雨,景色真是李清照但想起的詩詞卻是漠漠輕寒上小樓,想的太文藝之後怎麼去看都不再自然,停。
S在電話裡說「 你的心怎麼就不能再柔軟一點。」
她說的很大聲,有點像是責備。
笑著回說「 身體僵直的都快彎不下去如何柔軟,身心都隨著年紀越發堅硬固執,一直僵著嘗試柔軟也是疲倦。」
聽見S小聲的嘆氣,能知道這是他的柔軟、在為剛才的強硬道歉。
短暫的空白、誰也沒接話。好像又開始下起小雨,景色真是李清照但想起的詩詞卻是漠漠輕寒上小樓,想的太文藝之後怎麼去看都不再自然,停。
這幾日天氣好時會拉開窗簾,
躺在地板上享受正午的光。
書房暗了半邊天,永晝永夜、如此清晰分明,我與世界僅有一窗之隔。
久違的浮生感,簡直可說是鄉愁,看了幾眼意識幾乎就要遠去。
知道自己不願再多看便翻了個身、
像是
翻進蒼茫之地,
找不到自我、唯有野性匍匐在呼吸之上。

這幾日天氣好時會拉開窗簾,
躺在地板上享受正午的光。
書房暗了半邊天,永晝永夜、如此清晰分明,我與世界僅有一窗之隔。
久違的浮生感,簡直可說是鄉愁,看了幾眼意識幾乎就要遠去。
知道自己不願再多看便翻了個身、
像是
翻進蒼茫之地,
找不到自我、唯有野性匍匐在呼吸之上。

站在窗前看著片地餘暉,
亮的刺眼
所有街景像是雪白。
肌膚寒涼、思緒稀薄
像是暖陽裡的灰塵落不下來,卻看得清清楚楚。
呼吸像是機械式般重複的動作,
日以繼夜、偶爾感到厭倦。
不斷重複中,也偶爾能瞥見,
輕輕的東西、像是珍惜,
也無法確定。
站在窗前看著片地餘暉,
亮的刺眼
所有街景像是雪白。
肌膚寒涼、思緒稀薄
像是暖陽裡的灰塵落不下來,卻看得清清楚楚。
呼吸像是機械式般重複的動作,
日以繼夜、偶爾感到厭倦。
不斷重複中,也偶爾能瞥見,
輕輕的東西、像是珍惜,
也無法確定。
今天早上接近中午時他打來,語氣懨懨的說,「 上班才是真正的反社會行為,我寧願去野外打獵養活自己也不願整天被關在沈悶的大方格裡!」講的義氣凜然,語氣真誠,有點像是在哄騙自己。
掛電話後我心裡猜想,他最後還是懶懶地坐回辦公桌前。
想到那頹喪的模樣不自覺的笑了。
今天早上接近中午時他打來,語氣懨懨的說,「 上班才是真正的反社會行為,我寧願去野外打獵養活自己也不願整天被關在沈悶的大方格裡!」講的義氣凜然,語氣真誠,有點像是在哄騙自己。
掛電話後我心裡猜想,他最後還是懶懶地坐回辦公桌前。
想到那頹喪的模樣不自覺的笑了。
驚蟄到來的前幾日
總能察覺到空氣裡飄忽的沈悶。
微細的知會,
春分總是溫柔的。
那幾日心肺變的沈重,
是萬物沈沈的氣息、像是不願甦醒。
才剛睜眼,
感受到來自體內深層的拒絕,
心臟不願運轉、我也不願更迭。
在傍晚之間,
也不知道是多久、
也許有半刻鐘的時間,
世界格外明亮
比正午的光更柔軟明媚。
一切是金色的、
一切都寧靜的停在此刻,
像是被輕柔地包裹在琥珀裡,
被賜予永生。
可我怎麼
停不下來。
廚房燒的開水嗚嗚低鳴、
爐灶上的燉湯咕咕地滾、
電話那頭的友人正大肆抱怨。
當我抬頭往窗外望去,
只見自己在暮夜裡
幽幽浮沉。

驚蟄到來的前幾日
總能察覺到空氣裡飄忽的沈悶。
微細的知會,
春分總是溫柔的。
那幾日心肺變的沈重,
是萬物沈沈的氣息、像是不願甦醒。
才剛睜眼,
感受到來自體內深層的拒絕,
心臟不願運轉、我也不願更迭。
在傍晚之間,
也不知道是多久、
也許有半刻鐘的時間,
世界格外明亮
比正午的光更柔軟明媚。
一切是金色的、
一切都寧靜的停在此刻,
像是被輕柔地包裹在琥珀裡,
被賜予永生。
可我怎麼
停不下來。
廚房燒的開水嗚嗚低鳴、
爐灶上的燉湯咕咕地滾、
電話那頭的友人正大肆抱怨。
當我抬頭往窗外望去,
只見自己在暮夜裡
幽幽浮沉。
幾乎是要費盡心力才能在余光中看見,在細微的間隙中、清澈澄淨的自我,輕輕擺動。
我在疲憊中喜悅。砂礫碎石緩緩地落至岸上,我正赤身走過荒蕪的人生。
幾乎是要費盡心力才能在余光中看見,在細微的間隙中、清澈澄淨的自我,輕輕擺動。
我在疲憊中喜悅。砂礫碎石緩緩地落至岸上,我正赤身走過荒蕪的人生。
愛如此深沉,唯有沒能再見時才能被聽見。
你的名字
在深夜的街道上
迴盪,
走了一遍又一遍、家鄉沒能忘記你。
在沈沈的心上
迴盪,
走了、他們沒能忘記你。
你被深愛著,他們願你去更好更明亮的地方,走了、走了⋯
睡意又輕又薄像是遠處燈火闌珊、明明滅滅
天地明亮
心茫然。
愛如此深沉,唯有沒能再見時才能被聽見。
你的名字
在深夜的街道上
迴盪,
走了一遍又一遍、家鄉沒能忘記你。
在沈沈的心上
迴盪,
走了、他們沒能忘記你。
你被深愛著,他們願你去更好更明亮的地方,走了、走了⋯
睡意又輕又薄像是遠處燈火闌珊、明明滅滅
天地明亮
心茫然。
清晨似乎下過雨。
下午燉了蔬菜清湯。窗外暖的可疑,空氣是寒涼的、透進來的光像是假象;搭了帳篷在樓頂悠閒,什麼也沒想、躺著看’Klara and the Sun’,累了就放下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去看,就連自己也都不看一眼,沒想和自己獨處。
清晨似乎下過雨。
下午燉了蔬菜清湯。窗外暖的可疑,空氣是寒涼的、透進來的光像是假象;搭了帳篷在樓頂悠閒,什麼也沒想、躺著看’Klara and the Sun’,累了就放下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去看,就連自己也都不看一眼,沒想和自己獨處。
即使清晨有暖陽,在內依舊另開了一顆太陽,在最深處明亮。
點了一壺茶,茶杯是冷的、捂著。能明確地知道窗外的暖陽是熱的,像是這世界只能在想像中擁有、真實到生動,我卻無法長久。
即使清晨有暖陽,在內依舊另開了一顆太陽,在最深處明亮。
點了一壺茶,茶杯是冷的、捂著。能明確地知道窗外的暖陽是熱的,像是這世界只能在想像中擁有、真實到生動,我卻無法長久。
能聽見呼吸聲,有活著的真實感,意識到後只覺得更加疲憊。連打著這樣的廢文,也要抑制悲觀潰堤,人要多自虐。
能聽見呼吸聲,有活著的真實感,意識到後只覺得更加疲憊。連打著這樣的廢文,也要抑制悲觀潰堤,人要多自虐。
S年末跑來關心,雖然沒見到面但能肯定一定是拿著一杯Asahi。不知現在是幾點,冬日窗外總是暗的特別早,昏暗的書房沒捨得開燈,聽見外頭在下雨,不確定是下在我這裡,還是手機的另一頭。
S年末跑來關心,雖然沒見到面但能肯定一定是拿著一杯Asahi。不知現在是幾點,冬日窗外總是暗的特別早,昏暗的書房沒捨得開燈,聽見外頭在下雨,不確定是下在我這裡,還是手機的另一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