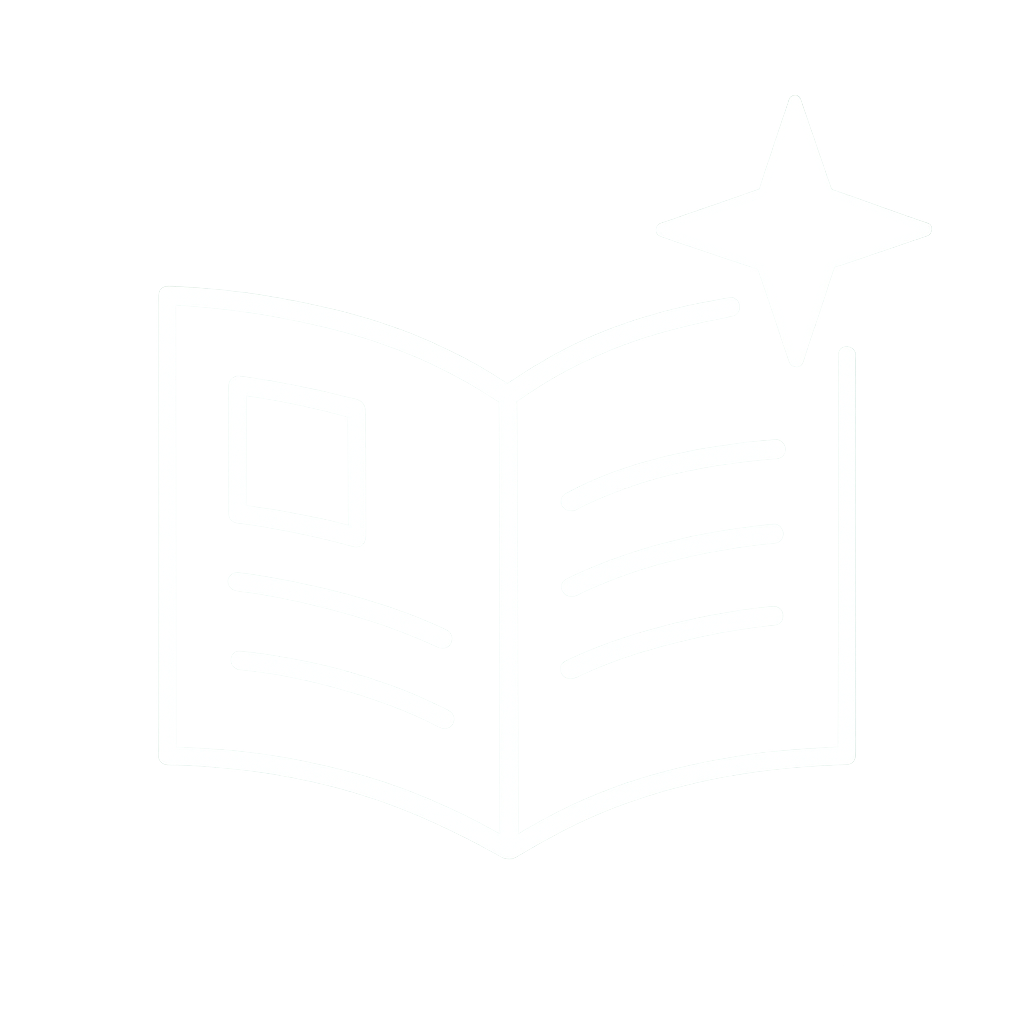真實的虛幻,海市蜃樓那般
大風,
像是蜷縮在金黃麥田,索性閉上眼
晃過許多影子、記不清,也沒來得及看清就散了。之後怎麼也想不起來,無端的惶恐、也沒睜開眼,想著自己忘了太多事,像是那些都是必然會被遺忘的。
必然,能記得的那一點成了全部、成了真實。想得太過痛苦了,只能接著想冰箱剩了什麼菜。




真實的虛幻,海市蜃樓那般
大風,
像是蜷縮在金黃麥田,索性閉上眼
晃過許多影子、記不清,也沒來得及看清就散了。之後怎麼也想不起來,無端的惶恐、也沒睜開眼,想著自己忘了太多事,像是那些都是必然會被遺忘的。
必然,能記得的那一點成了全部、成了真實。想得太過痛苦了,只能接著想冰箱剩了什麼菜。
阿嬤也塞了一些菊苣說喜歡吃沙拉這個也拿一點。
抱了一大把的菜,美好的週四清晨。
( 回家馬上烤了kale chips、大姐說太鹹了,也不知道怎麼抱持脆度🆘 不知道還有什麼食譜能夠消耗非常大把的羽衣甘藍?)

阿嬤也塞了一些菊苣說喜歡吃沙拉這個也拿一點。
抱了一大把的菜,美好的週四清晨。
( 回家馬上烤了kale chips、大姐說太鹹了,也不知道怎麼抱持脆度🆘 不知道還有什麼食譜能夠消耗非常大把的羽衣甘藍?)
穿著薄襯衫站在路燈下等計程車,知道自己看起來可能狼狽但也無心關切,只覺得身體空的不像話。
窗景不斷後退,在半開的窗戶間聽著蓄滿雜音的台語廣播,黃光一晃一晃擦過,明暗明暗,很drama的想著世間所有的事物我都看不清,突然一個瞬間意識全部聚焦眼前,無來由的感到惶恐,但也就那一下。
大拆大檢過後就很常這樣恍惚,總覺得面目全非但也懶得收拾。回家見大姐在客廳打電動、只開了半邊的燈,他頭也沒抬說「吃了沒,留了飯菜在電鍋。」
想著幾年後在很平常的瞬間可能會想起這一幕。



穿著薄襯衫站在路燈下等計程車,知道自己看起來可能狼狽但也無心關切,只覺得身體空的不像話。
窗景不斷後退,在半開的窗戶間聽著蓄滿雜音的台語廣播,黃光一晃一晃擦過,明暗明暗,很drama的想著世間所有的事物我都看不清,突然一個瞬間意識全部聚焦眼前,無來由的感到惶恐,但也就那一下。
大拆大檢過後就很常這樣恍惚,總覺得面目全非但也懶得收拾。回家見大姐在客廳打電動、只開了半邊的燈,他頭也沒抬說「吃了沒,留了飯菜在電鍋。」
想著幾年後在很平常的瞬間可能會想起這一幕。
這幾日天氣好時會拉開窗簾,
躺在地板上享受正午的光。
書房暗了半邊天,永晝永夜、如此清晰分明,我與世界僅有一窗之隔。
久違的浮生感,簡直可說是鄉愁,看了幾眼意識幾乎就要遠去。
知道自己不願再多看便翻了個身、
像是
翻進蒼茫之地,
找不到自我、唯有野性匍匐在呼吸之上。

這幾日天氣好時會拉開窗簾,
躺在地板上享受正午的光。
書房暗了半邊天,永晝永夜、如此清晰分明,我與世界僅有一窗之隔。
久違的浮生感,簡直可說是鄉愁,看了幾眼意識幾乎就要遠去。
知道自己不願再多看便翻了個身、
像是
翻進蒼茫之地,
找不到自我、唯有野性匍匐在呼吸之上。

驚蟄到來的前幾日
總能察覺到空氣裡飄忽的沈悶。
微細的知會,
春分總是溫柔的。
那幾日心肺變的沈重,
是萬物沈沈的氣息、像是不願甦醒。
才剛睜眼,
感受到來自體內深層的拒絕,
心臟不願運轉、我也不願更迭。
在傍晚之間,
也不知道是多久、
也許有半刻鐘的時間,
世界格外明亮
比正午的光更柔軟明媚。
一切是金色的、
一切都寧靜的停在此刻,
像是被輕柔地包裹在琥珀裡,
被賜予永生。
可我怎麼
停不下來。
廚房燒的開水嗚嗚低鳴、
爐灶上的燉湯咕咕地滾、
電話那頭的友人正大肆抱怨。
當我抬頭往窗外望去,
只見自己在暮夜裡
幽幽浮沉。

驚蟄到來的前幾日
總能察覺到空氣裡飄忽的沈悶。
微細的知會,
春分總是溫柔的。
那幾日心肺變的沈重,
是萬物沈沈的氣息、像是不願甦醒。
才剛睜眼,
感受到來自體內深層的拒絕,
心臟不願運轉、我也不願更迭。
在傍晚之間,
也不知道是多久、
也許有半刻鐘的時間,
世界格外明亮
比正午的光更柔軟明媚。
一切是金色的、
一切都寧靜的停在此刻,
像是被輕柔地包裹在琥珀裡,
被賜予永生。
可我怎麼
停不下來。
廚房燒的開水嗚嗚低鳴、
爐灶上的燉湯咕咕地滾、
電話那頭的友人正大肆抱怨。
當我抬頭往窗外望去,
只見自己在暮夜裡
幽幽浮沉。

附近的攤販臉上有些嫌棄、也許是哀怨。上面發生了什麼似乎與地面下的人無關,他們僅是深陷於生活當中,無人仰頭嘆息。冬日的暖陽照著,一切是如此清晰無疑,在大自然中似乎本就沒有珍惜這一回事,純粹原始的無情對文明社會來講是一種威脅,共生便是一場鴻門宴。
大聲落下的粉塵、無聲的抗爭,你的見證到此為止,但這不會是歷史的終結。我也見證了你的過往、你的當下。
寧靜的葬禮,風大的簡直像是荒原,而我清楚的意識到—我才是這裡的異鄉人。


附近的攤販臉上有些嫌棄、也許是哀怨。上面發生了什麼似乎與地面下的人無關,他們僅是深陷於生活當中,無人仰頭嘆息。冬日的暖陽照著,一切是如此清晰無疑,在大自然中似乎本就沒有珍惜這一回事,純粹原始的無情對文明社會來講是一種威脅,共生便是一場鴻門宴。
大聲落下的粉塵、無聲的抗爭,你的見證到此為止,但這不會是歷史的終結。我也見證了你的過往、你的當下。
寧靜的葬禮,風大的簡直像是荒原,而我清楚的意識到—我才是這裡的異鄉人。
身體卻如往常誠實,紅痕佈滿全身像是對我埋怨。
麻煩與忙碌全都太過具體太過寫實、但並不真實。半夜,一個人窩在廚房吃著回熱的義大利麵,熱了牛奶心急不小心被燙到,’啊!’了一聲,那一瞬間像是有了重量,所有散落的意識回歸,突然變得沈重。
意識全都在等著這個停頓。
我站在明火前看著自己卻幫不上忙,情緒沒能跟上,只能任由淚水低回喃喃。


身體卻如往常誠實,紅痕佈滿全身像是對我埋怨。
麻煩與忙碌全都太過具體太過寫實、但並不真實。半夜,一個人窩在廚房吃著回熱的義大利麵,熱了牛奶心急不小心被燙到,’啊!’了一聲,那一瞬間像是有了重量,所有散落的意識回歸,突然變得沈重。
意識全都在等著這個停頓。
我站在明火前看著自己卻幫不上忙,情緒沒能跟上,只能任由淚水低回喃喃。
ポケが日、宇宙はそれに照らされて動いてる。
これが宇宙の真理。
😔🤜🏻🤛🏻❤️🩹

ポケが日、宇宙はそれに照らされて動いてる。
これが宇宙の真理。
😔🤜🏻🤛🏻❤️🩹
想吃潤餅冰淇淋,沒帶錢只能用耍賴花招求大姊請客,順利get!

想吃潤餅冰淇淋,沒帶錢只能用耍賴花招求大姊請客,順利get!
1.
散步的途中撞見情侶(也許是)吵架,男的講的很大聲耳根都發紅了,「我講了你也不信!你到底想要我怎樣!我不講你也生氣!想逼瘋我嗎!」
有點尷尬,想著要不要回頭走原路。
真是了無新意,好像全球所有人口都在吵同樣的問題。不過都是為了那點幸福感,太過虛幻,值得嗎,不禁在心底疑問起。
幸福感是人的集體幻覺嗎。
2.
橋下的拼接鐵片簡直就像大型俄羅斯方塊,這種不禁意的裝置藝術莫名令人愉悅。
自己一人在車上笑的很開懷。

1.
散步的途中撞見情侶(也許是)吵架,男的講的很大聲耳根都發紅了,「我講了你也不信!你到底想要我怎樣!我不講你也生氣!想逼瘋我嗎!」
有點尷尬,想著要不要回頭走原路。
真是了無新意,好像全球所有人口都在吵同樣的問題。不過都是為了那點幸福感,太過虛幻,值得嗎,不禁在心底疑問起。
幸福感是人的集體幻覺嗎。
2.
橋下的拼接鐵片簡直就像大型俄羅斯方塊,這種不禁意的裝置藝術莫名令人愉悅。
自己一人在車上笑的很開懷。

I had only wanted to stay invisible, that is and always will be my only wish.
.
生日大禮便是終於出手買了二手的Stargazerガンダム!
( murmur:半價而且還附了特典,我的客家血統在咆哮嘶吼。)


I had only wanted to stay invisible, that is and always will be my only wish.
.
生日大禮便是終於出手買了二手的Stargazerガンダム!
( murmur:半價而且還附了特典,我的客家血統在咆哮嘶吼。)
『 我們這樣也算是WFH的一種吧,work from hospital。』
⋯^_^??
這種時候還有心情講冷笑話還真是令人欣慰ʕ ᵔᴥᵔ ʔ ꐦ

『 我們這樣也算是WFH的一種吧,work from hospital。』
⋯^_^??
這種時候還有心情講冷笑話還真是令人欣慰ʕ ᵔᴥᵔ ʔ ꐦ
昨日太勞累忘了準備今日的午餐,正好路過一間饅頭店卻都只有肉包的選項,唯一能吃的只有紅豆口味。
真的是非常奇妙的食物!並不是我認知裡的饅頭。
麵皮的口感輕柔中帶點紮實感,底部被蒸烤至有輕微的焦香,紅豆在鍋中與砂糖一起不斷地拌炒直至沙狀但同時又保留著豆粒的口感。
剛出爐還冒著蒸氣的時候一口咬下,內餡的紅豆香氣一瞬在口中四溢。雖然燙口,但像包子饅頭這種美食不就是要剛出籠時毫不猶豫的一口咬下,然後在微微地張嘴哈出熱氣嗎?
これは人生で一番幸せな瞬間!

昨日太勞累忘了準備今日的午餐,正好路過一間饅頭店卻都只有肉包的選項,唯一能吃的只有紅豆口味。
真的是非常奇妙的食物!並不是我認知裡的饅頭。
麵皮的口感輕柔中帶點紮實感,底部被蒸烤至有輕微的焦香,紅豆在鍋中與砂糖一起不斷地拌炒直至沙狀但同時又保留著豆粒的口感。
剛出爐還冒著蒸氣的時候一口咬下,內餡的紅豆香氣一瞬在口中四溢。雖然燙口,但像包子饅頭這種美食不就是要剛出籠時毫不猶豫的一口咬下,然後在微微地張嘴哈出熱氣嗎?
これは人生で一番幸せな瞬間!
它們隨著我爬上米開朗基羅廣場見證最美的日落、在里昂金頭公園的草皮上慵懶的野餐、在臺北午夜的便利商店喝著草莓香料過濃的牛乳。
寄出的明信片裡寫著日常,那黑白之間小心翼翼藏抑著未能訴說的情感。
那些無名的日常與我生活多年,而我從不過問它們的名諱。是在很後來,在我們不再聯絡之時,它們才在我耳邊小聲地說著 —— 我們名為愛。

它們隨著我爬上米開朗基羅廣場見證最美的日落、在里昂金頭公園的草皮上慵懶的野餐、在臺北午夜的便利商店喝著草莓香料過濃的牛乳。
寄出的明信片裡寫著日常,那黑白之間小心翼翼藏抑著未能訴說的情感。
那些無名的日常與我生活多年,而我從不過問它們的名諱。是在很後來,在我們不再聯絡之時,它們才在我耳邊小聲地說著 —— 我們名為愛。
見了面依然像是單口相聲,友人開口而我也只是坐在對面有時做出反應與回應,乍看上像是我對生活漠不關心導致我並沒有什麼能夠分享的事。打從心底希望對方能有閱讀腦內的功能,這樣我也就不必思考不必開口。
內心有想要喧囂的慾望,可言語卻似頓在喉間,而掙扎地最後從口中溜出的也只剩幾個狀聲詞。
若是用英文的話,我大概能抱怨到對方再也不想聽下去,但不知為何中文給人一種彆扭且難以敘述的羞恥感,索性就閉口而不談。
murmur: 雖對友人抱持的情感已然淡去,但每次見到面內心都在吶喊 ”超ヤバ!美人だ、好き… ”

見了面依然像是單口相聲,友人開口而我也只是坐在對面有時做出反應與回應,乍看上像是我對生活漠不關心導致我並沒有什麼能夠分享的事。打從心底希望對方能有閱讀腦內的功能,這樣我也就不必思考不必開口。
內心有想要喧囂的慾望,可言語卻似頓在喉間,而掙扎地最後從口中溜出的也只剩幾個狀聲詞。
若是用英文的話,我大概能抱怨到對方再也不想聽下去,但不知為何中文給人一種彆扭且難以敘述的羞恥感,索性就閉口而不談。
murmur: 雖對友人抱持的情感已然淡去,但每次見到面內心都在吶喊 ”超ヤバ!美人だ、好き… ”
出了名愛抱怨之國的同事:t'es sérieuse! tu manges un sandwich avec des baguettes? c'est un peu fou, non?
現在大家都認為亞洲人不管吃什麼都用筷子了( 一旁的臺灣同事正盡力挽救這個刻板印象。)

出了名愛抱怨之國的同事:t'es sérieuse! tu manges un sandwich avec des baguettes? c'est un peu fou, non?
現在大家都認為亞洲人不管吃什麼都用筷子了( 一旁的臺灣同事正盡力挽救這個刻板印象。)
扣子解到一半的襯衫依舊固執的掛在身上,褲子一側的口袋內塞著小方巾,本該在裡面的手機則被丟棄在架上的杯口裡。
這應該可以被列入下班奇妙百景裡前10名了吧。
.
又在深夜時段做料理,母親前幾日送了幾顆比我的臉還大的臺灣酪梨。想著如果混著蕃茄丁、橄欖油、檸檬然後加在麵包裡應該會好吃的不得了吧,所以做了一大片Focaccia(加了在義大利買的辛香料,那時隨性而買的一直沈睡在櫥櫃的下層內,今日終於派上用場了!)
還特別加了日本同事教的’すべてを美味しく変える魔法’( 自己一個人在深夜裡對著麵包自言自語⋯ )

扣子解到一半的襯衫依舊固執的掛在身上,褲子一側的口袋內塞著小方巾,本該在裡面的手機則被丟棄在架上的杯口裡。
這應該可以被列入下班奇妙百景裡前10名了吧。
.
又在深夜時段做料理,母親前幾日送了幾顆比我的臉還大的臺灣酪梨。想著如果混著蕃茄丁、橄欖油、檸檬然後加在麵包裡應該會好吃的不得了吧,所以做了一大片Focaccia(加了在義大利買的辛香料,那時隨性而買的一直沈睡在櫥櫃的下層內,今日終於派上用場了!)
還特別加了日本同事教的’すべてを美味しく変える魔法’( 自己一個人在深夜裡對著麵包自言自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