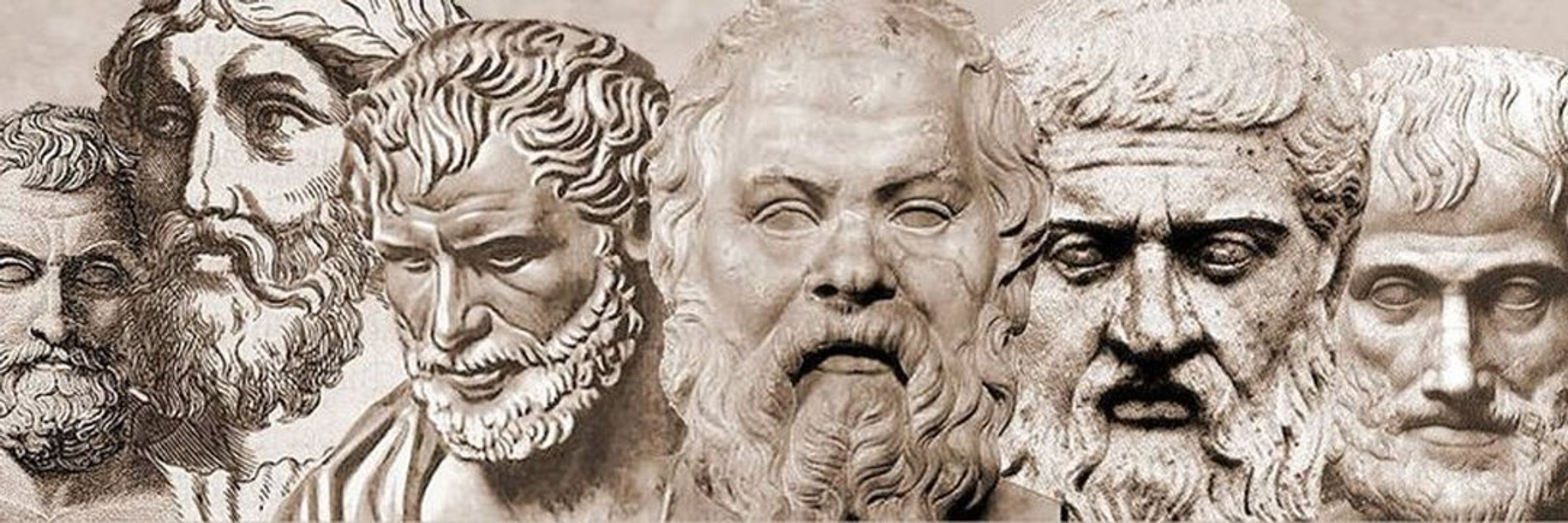
用英文回答不仅显得有点不礼貌,更糟的是容易让人觉得你是在装高贵。可惜的是,你的“Chinglish”实在太尴尬。
比如你写的 “in some respect” 就是错误的,标准说法应是:
It is, in some respects, worse than China.
或者更自然:
In some respects, it’s worse than China.
用英文回答不仅显得有点不礼貌,更糟的是容易让人觉得你是在装高贵。可惜的是,你的“Chinglish”实在太尴尬。
比如你写的 “in some respect” 就是错误的,标准说法应是:
It is, in some respects, worse than China.
或者更自然:
In some respects, it’s worse than China.
理念是“建筑图纸”
信仰是“承建意志”
理性是“工程逻辑”
而存在是“那片真正可以打地基的土地”。 没有土地,一切结构就只是漂浮的。
你理解理念、信仰、理性,是因为它们可以被你分析或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们之所以能被你理解、被你相信,本身就是一种“现身”的现象?你有没有想过,它们怎样才被你所遭遇?那就是我说的“存在”。
理念是“建筑图纸”
信仰是“承建意志”
理性是“工程逻辑”
而存在是“那片真正可以打地基的土地”。 没有土地,一切结构就只是漂浮的。
你理解理念、信仰、理性,是因为它们可以被你分析或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们之所以能被你理解、被你相信,本身就是一种“现身”的现象?你有没有想过,它们怎样才被你所遭遇?那就是我说的“存在”。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真要选一个专业作为基础,我推荐物理专业。一个具备坚实自然科学背景、又懂一些哲学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什么普遍规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与路径,重要的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它。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真要选一个专业作为基础,我推荐物理专业。一个具备坚实自然科学背景、又懂一些哲学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什么普遍规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与路径,重要的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它。
如果你打算攻读哲学的高等学位,并希望将哲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比如将来进入大学任教,那么读哲学专业基本上是唯一的路径,这一点没有太多选择。
但如果你对哲学的兴趣主要出于个人热爱,而不是为了从事学术职业,我个人认为就没有必要专门去攻读哲学硕士。哲学是一门高度开放的学科,它并不一定依赖于学院体系才能真正理解。事实上,有时候在体制内接受专业训练,反而会限制思维的开放性,使人容易陷入某种学派的偏狭。以我所认识的...
如果你打算攻读哲学的高等学位,并希望将哲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比如将来进入大学任教,那么读哲学专业基本上是唯一的路径,这一点没有太多选择。
但如果你对哲学的兴趣主要出于个人热爱,而不是为了从事学术职业,我个人认为就没有必要专门去攻读哲学硕士。哲学是一门高度开放的学科,它并不一定依赖于学院体系才能真正理解。事实上,有时候在体制内接受专业训练,反而会限制思维的开放性,使人容易陷入某种学派的偏狭。以我所认识的...
许多人对“核辐射”与“核泄漏”的概念几乎一无所知,将两者混为一谈。他们不了解核物理中涉及的基本原理,如放射性同位素的特性、半衰期的长短、辐射剂量的衡量单位等。由于这些概念本身较为抽象且专业,普通公众往往难以深入理解,从而容易被片面信息或恐慌情绪误导。
许多人对“核辐射”与“核泄漏”的概念几乎一无所知,将两者混为一谈。他们不了解核物理中涉及的基本原理,如放射性同位素的特性、半衰期的长短、辐射剂量的衡量单位等。由于这些概念本身较为抽象且专业,普通公众往往难以深入理解,从而容易被片面信息或恐慌情绪误导。
关于阿奎那,他在《神学大全》中确实论述了“全知与自由”的问题。他认为神的“预知”并不妨碍人的自由,因为神在永恒中“同时地”知晓一切,并非像我们一样在时间中“前后推演”。这是一个中世纪对“永恒与时间”差异的辩证理解,也非常精彩。但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已不仅仅是解释神如何“知而不控”,而是追问:“为何存在之中还有‘自由生成’的空间?”
这个问题,可能只有当我们重新理解“信仰的对象不是神,而是生成性的存在本身”时,才真正打开出路。
@shadowking111.bsky.social
关于阿奎那,他在《神学大全》中确实论述了“全知与自由”的问题。他认为神的“预知”并不妨碍人的自由,因为神在永恒中“同时地”知晓一切,并非像我们一样在时间中“前后推演”。这是一个中世纪对“永恒与时间”差异的辩证理解,也非常精彩。但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已不仅仅是解释神如何“知而不控”,而是追问:“为何存在之中还有‘自由生成’的空间?”
这个问题,可能只有当我们重新理解“信仰的对象不是神,而是生成性的存在本身”时,才真正打开出路。
@shadowking111.bsky.social
这正是我尝试从“神本主义”(theocentrism)迈向“生成本体论”(ontogenesis)的出发点:
在你提出的框架中,神是世界的解释前提,而人的自由是被允许的可能;
在我试图展开的“生成信仰”中,存在本身尚未被设定,而是从“无”中动态生成;
这正是我尝试从“神本主义”(theocentrism)迈向“生成本体论”(ontogenesis)的出发点:
在你提出的框架中,神是世界的解释前提,而人的自由是被允许的可能;
在我试图展开的“生成信仰”中,存在本身尚未被设定,而是从“无”中动态生成;
从生成出发:非神论宇宙观中的信仰重建
sophosletter.substack.com/p/1b2?r=5te4ke
宇宙的起源:无中生有(Something from Nothing)
sophosletter.substack.com/p/something-...
本体与结构:哲学的分界线与生成的根源
sophosletter.substack.com/p/ecf?r=5te4ke

从生成出发:非神论宇宙观中的信仰重建
sophosletter.substack.com/p/1b2?r=5te4ke
宇宙的起源:无中生有(Something from Nothing)
sophosletter.substack.com/p/something-...
本体与结构:哲学的分界线与生成的根源
sophosletter.substack.com/p/ecf?r=5te4ke
哲学深藏于科学之中——科学方法本身就源于哲学;
哲学融入宗教之中——神学体系就是对信仰的哲学化理解;
哲学更渗透于人的生活——因为人是一种不断追问“应该怎样活”的存在。
你也许没有系统地“学过哲学”,但你已经在用哲学生活。你所缺的不是哲学,而是对哲学的自觉。
这正是我在中文世界里推广哲学的初心所在——不是因为哲学高深,而是因为它太被忽视、太被误解、也太被需要了。
哲学深藏于科学之中——科学方法本身就源于哲学;
哲学融入宗教之中——神学体系就是对信仰的哲学化理解;
哲学更渗透于人的生活——因为人是一种不断追问“应该怎样活”的存在。
你也许没有系统地“学过哲学”,但你已经在用哲学生活。你所缺的不是哲学,而是对哲学的自觉。
这正是我在中文世界里推广哲学的初心所在——不是因为哲学高深,而是因为它太被忽视、太被误解、也太被需要了。
因此,开放的、民主的社会离不开哲学,因为它需要不断对价值冲突进行反思与协调。而专制社会则恰恰回避公共理性,它以强制性权威取代了思辨与共识,因而对哲学的需求也趋近于零。所以中文世界里(包括任何专制社会)不需要哲学——因为反思、质疑、公共讨论恰恰是被压制的。
因此,开放的、民主的社会离不开哲学,因为它需要不断对价值冲突进行反思与协调。而专制社会则恰恰回避公共理性,它以强制性权威取代了思辨与共识,因而对哲学的需求也趋近于零。所以中文世界里(包括任何专制社会)不需要哲学——因为反思、质疑、公共讨论恰恰是被压制的。
因此,正义作为理念是恒定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方向感;而正义的意义,则是在实践与时间性中生成的,是对具体情境中人类合作、冲突、差异与期望的回应。理念与生成之间并非矛盾,而是一种结构性张力:理念设定了方向,生成使其成显。
这个观点在我正在写作的《意义形上学》中已有充分展开。
因此,正义作为理念是恒定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方向感;而正义的意义,则是在实践与时间性中生成的,是对具体情境中人类合作、冲突、差异与期望的回应。理念与生成之间并非矛盾,而是一种结构性张力:理念设定了方向,生成使其成显。
这个观点在我正在写作的《意义形上学》中已有充分展开。
正义如果被当作一种“评估机制”,那么它的运作便必须具有情境依赖性:即它所评估的正当性,必须根据当下各方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来调整。在这种理解下,正义成为一种动态生成的结构,其机制不是静态原则的应用,而是不断修正的共识建构过程。这使得它更像是一种“过程中的合理性”而非“本体上的绝对性”。
此外,我们无法向他人许诺自己所无法理解的利益。这一点触及到契约理论的根本局限:一个有效的合作关系,必须建立在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充分理解之上;一旦环境发生变化,
正义如果被当作一种“评估机制”,那么它的运作便必须具有情境依赖性:即它所评估的正当性,必须根据当下各方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来调整。在这种理解下,正义成为一种动态生成的结构,其机制不是静态原则的应用,而是不断修正的共识建构过程。这使得它更像是一种“过程中的合理性”而非“本体上的绝对性”。
此外,我们无法向他人许诺自己所无法理解的利益。这一点触及到契约理论的根本局限:一个有效的合作关系,必须建立在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充分理解之上;一旦环境发生变化,

